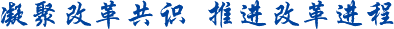不清算原罪,也不放弃价值判断
发稿时间:2017-02-10 10:45:15 来源:凤凰评论 作者:秦晖
8月,非虚构作家雪珥《危险关系:晚清转型期的政商赌局》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近日,该书出版座谈会举行。与会学者秦晖、吴思、王焱、蔡霞等人,与雪珥就政商关系问题做了探讨。以下为秦晖的与会发言。
这本书里的故事写得非常精彩,而且也非常有意义。我没有专门研究过晚清史,不知道有这么多的故事,看了以后,的确觉得既有传奇色彩也有分析价值。
事实上,类似的故事应该很不少,从《货殖列传》桑弘羊开始,历代都有,主要是对这种事怎么看。我对这些事情进行道德批判乃至鼓动清算持反对意见的,尤其是在当下,为了使改革顺利,我认为能不清算最好就不清算。但是作为观察历史的一个价值维度,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个判断,因为假如这个东西是正常的,我们就不需要改革了,需要改革就是想走出这个东西。
常说人是有原罪的,实际上反过来讲权力也是有原罪的,不光是资本,权力和资本双方都有原罪。现在一个主流话语就是对辛亥革命的批评。对辛亥革命的批评,我发现主要不是对辛亥本身,武昌起义没有多少人批评,因为这个起义没有多少负面的东西。大部分的批评都来自对保路运动的批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所谓民营公司有原罪,因为它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假如真的要做这样一种判断,那么清廷采取措施把它没收以后,真的还给老百姓就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自己吞掉了这个东西,就有很大的问题,黑吃黑,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既然是黑吃黑,所以就可以这样?假如你真的认为国有资产来路不正,是抢别人的,只能得出两个言论:一个是应该换给苦主,抢了谁应该还给谁。还有一个是,假如我们又做不到这一点,比如时间久了,已经无法追溯了,诺齐克讲的正义链条不可能完整、不可能实行矫正正义,怎么办?说实在的,在这种情况下那只能把这个哪怕来自不公正的东西作为一个公众的财产服务于公众,比如搞社会保障。如果这个时候你又把它吞到某一个人的口袋里去了,毫无疑问,这当然比原来的邪恶上面又加了一层邪恶。不能说这个东西是抢来的,现在把它吞掉了。后来国进民退大家很有意见,大家知道在2010年前后,中国就开始有清算煤老板,国进民退搞得很厉害,后来很多人就很有意见了。
我记得有位朋友说:你们都认为很悲观,我很乐观,你别看现在国进民退,他们把老百姓的财产抢去了以后,他们也不打理的,最后还是被他们糟蹋完了、贪污完了。若干年以后,你会发现国有资产的比例还会下降,降得比现在还要低都可能,所以我对这个事我不悲观。
我听了以后很悲哀,假如你作为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对国进民退不悲观,因为国进民退还是通过贪污变成私有财产。同样,作为一个左派可以对私有化不悲观,私有化有什么可悲观的?现在那些老板,我把他养肥了,最后把他全都宰了,又抢回来,不就完了?抢到国库里,再揣进我的口袋,国库揣完了,再抢一轮,抢完了就再揣。如果中国经济是这么循环,我们岂不是跌入万丈深渊了?所以不管是抢还是偷都要谴责,抢劫式的公有化和偷盗式的私有化,罪恶就是罪恶。现在要真的推动改革,就是要走出这种状况。而走出这种状况,从来不能依靠这些危险的游戏。不是你这本书大家才知道这个危险,红顶商人被宰的例子太多了,从桑弘羊一直到胡雪岩,几乎所有的商人都这样。但是危险不能带来改革,尽管这种游戏一开始就危险,危险了两千年我们也没有走出这个东西。所以所谓的改革还是要采取措施,制止这种循环,制止钱买权的循环。
现在很多人老是基于某一种意识形态,把公有化和私有化对立起来,一些右派朋友反对公有化,就认为不管怎么样,用什么手段搞私有化都是可以的;一些左派朋友反对私有化,认为不管怎么抢老百姓的财产搞公有化也是可以的。其实这两种东西同样都是罪恶,一个现代国家既不可能用抢劫的办法搞公有化,也不可能用偷盗的办法搞私有化。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在一个民主体制下,倒真的可以讲我们到底是国家干预多一些还是自由放任多一点,福利国家多一点还是自由竞争多一点,甚至国有财产多一点还是民有财产多一点。但不管是国有还是民有,都得取之有道,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国家也爱财,国家的财也是需要取之有道。
还有一点,把这些事在历史上当作一种常态来讲,可能是受到一个意识形态的影响,就是我们以前长期讲的“原始积累”。马克思一直讲原始积累,资本来到世间就如何如何。这个事情就为很多邪恶的事情制造了理由。当年,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就是这样搞起来的,结果苏联有一帮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就说社会主义也可以这样搞。马克思其实没有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马克思讲的“原始积累”根本就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以前有一种原始积累。最早是亚当·斯密讲的,他讲的不是原始,而是预先,是市场经济以前已经抢过一次了,第一笔钱是抢的,这第一笔钱根本就不是资本主义,但不管怎么样抢来以后,用这个钱作为本钱做买卖。后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说:“社会主义的第一笔钱也应该是抢的。”实际上,原始积累有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就是圈地运动;还有一种是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那就是抢农民。当时就有人讲,“原始积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当作普遍现象,只是讲英国是这样的,而且用的是“可能是这样”的表述。后来所有人都说这个东西不是普遍的,很多人说北欧不是这样的,东亚也不是这样的,很多人说这个事情,第一本身不是资本主义,甚至也不是早期的资本主义,这个也不是普遍现象,把它变成所谓的社会主义就更不行了。
我记得90年代有一部讲深圳起飞初期的电视政论片,其中就提到很多深圳早期的一些事,民工住在工棚里,工棚是上锁的,结果一场火灾烧死了几十个人。然而话题一转,说这些事情是难免的,英国有羊吃人,羊吃了成千上万的人,我们现在付出这点代价不算什么。这简直是胡说,所谓的“羊吃人”只不过是一个形容词而已,而圈地运动,说实在的,现在被丑化了,圈地运动不是马克思讲的那样一个过程,圈地运动不是圈老百姓的土地,而是农村公社的场地给取消了,原来可以公共放牧的现在不给公共放牧,圈起来了,圈起来以后,很多人要像原来的村舍要付出代价,当然有些不公平是肯定的,但是圈地运动绝大部分是跑马占圈,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没有造成大量死人,所谓“羊吃人”只是一个说法。但这个说法大家听惯以后,觉得搞市场经济就是这么搞的,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历史也不是这样的。
还有一点,如果没有价值判断好像从来没有人做得到,包括雪珥兄你自己就有一些价值判断在里头。不过我觉得你的价值判断有一些很有趣——你的批判对象基本上是老百姓,统治者基本上没有什么责任。老百姓当然有可恶的地方,这点毫无疑问。不过说实在的,如果只骂暴君不骂暴民,只骂暴民不骂暴君都是不对的。
前段时间你有篇文章挺有意思,你讲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没有亲情的民族,为了赚钱可以不顾家。很多人讲中国人是重亲情的、是重伦理的,你觉得不是,认为中国人都是把家丢了不管而出来捞钱。这个现象当然有,尤其是最近留守儿童悲剧发生那么多,而且报道越来越密集。但中国人真的愿意这样子吗?不说别的,当年重庆市副市长就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中国之所以没有贫民窟,是因为我们的制度用两栖人的方法解决了问题,不允许他们用低成本进入城市,那就是壮工出来打工,把家人留在农村,这样城里就不会有很多穷人。但是所谓的“两栖人”不就是造成家庭离散的原因吗?现在造成三亿多人的家庭离散完全是一个制度现象,哪个老百姓不喜欢老婆孩子热炕头?如果你让老百姓选择,他们愿意住在一个穷窝里还是楼房里头但是家庭分离,绝大多数老百姓都会选择前者的。
我有一个最深的印象,上海改革以前住房非常紧张,三代同堂、四代同堂普遍存在。但是改革前的三十年中,只有三年时间,上海人均住房面积得到了提高,哪三年?从1969年到1972年。人均住房面积提高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把这些孩子赶走了,赶走了以后,人均住房提高了。但当时上海人羡慕的是哪种人?羡慕的是全家挤在一个窝窝里。孩子被赶走了、住房面积增加了的人都被大家看成是不幸者,没有人喜欢把孩子赶到乡下去,从而改善住房条件,全世界的人都不会这样想。这完全是制度安排造成的结果,中国人不可能为了钱而不顾家的。但如果把这个事情作为一种文化解释,我觉得恐怕是有一点问题的。当然我也不赞成把这个事情说成是某个统治者的罪过,因为说实在的,这些事情真的要讲归结于什么,最终还是得归结于制度方面的因素,制度方面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