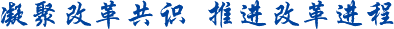呈现多元化面相的明代文化
发稿时间:2024-07-10 10:06:59 来源:《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作者:陈宝良
明代正值社会转型时期,是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开端。就明代文化而论,晚明堪称最有活力、最有生气、最有解放精神的时代。进而言之,明朝人思想之活跃,兴趣之广泛,视野之开阔,均是前无古人的,以致出现了一些奇谈怪论。
在明代的知识人群体中,开始对儒家传统道德进行彻底的反省,进而为自出机杼的新说奠定思想基础
明代怪论的出现至少可以证明,在明代的知识人群体中,开始对儒家传统道德进行彻底的反省,进而为自出机杼的新说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晚明的知识人群体中,出现了不乏新见的论著,如贺道星之《危言》,袁宏道之《狂言》,李贽之《焚书》,顾大韶之《放言》。从这些书名或篇名不难发现,他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言论或许会因为自出机杼而不被传统或世俗之士所见容。
一是怀疑精神。如李之藻认为,人具怀疑精神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人只要“求诸自心而不得”,或者“质诸习闻习见而不合”,势必会产生怀疑。当然,所谓的“疑”,可以分为“正疑”与“妄疑”两种,他所取的仅仅是“正疑”而已,但李之藻提出的“正疑”,势必导致这样一种认知,即“道”未必“备于古”,“经”未必“尽于圣”。在明人思想中,弥漫着一股疑古的思潮。这种思潮,先由“疑传”开其端,进而发展到“疑经”。一至“翼经”“续经”说的提出,更是说明明人已具一种“经自我作”的思想。
二是创新精神。明代学术的最大特点,就是自出机杼,凡是前人说过的话,便不屑再说,却总是要另出一番臆说。从清儒李光地的记载可知,明末有一位耆老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孔子之书,不过是立教如此,非是要人认以为实。”这种别出己见的风气,始于嘉靖以后,尤其是王阳明开启了这一派的学问,进而在明末蔚为一股风潮。在明末,无论是浅学小生,还是著名学者,无不“以訾毁先辈为豪大,以诋讥宋儒为名通”,甚至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一种“时尚”。
变者,即不再恪守传统,而是持一种“是今非古”之论
明代文化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面相。这种“多样性”,大抵可以用博、杂二字加以形容。
说其博,不仅限于知识储备的弘博,更是指明人有着包容不同思想、不同见解的胸怀。就知识结构的弘博而言,明人兴趣广泛,喜于务博,几已成为一种风气。尤为可贵者,在明人的知识构成中,已经开始会通古今、会通儒佛道、会通儒耶。以会通古今为例,丘濬主张将“稽古”与“近思切己”相结合,显然是将古今牵于一线。以会通儒佛道为例,晚明儒佛道三教合一之论甚嚣尘上,佛教开始向科举八股文渗透。以会通儒耶为例,晚明的学者并非止步于将儒学与基督教合流,而是在此之上更进一步,在文化上达臻会通中西的境界。如李之藻认为,“学问无穷,圣化无外”,对于来自西方的异文化,不妨采取“并蓄兼收”的态度,以昭显“九州同文之盛”;徐光启更是提出了“会通超胜”这一颇有前瞻性的主张,建议借助于翻译—会通—超胜这一过程,吸收西方文化,乃至超越西方文化。
说其杂,主要是指文化、知识弘博背后的乱象,甚至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明人学问,绝非清儒所指摘的“空疏”,而是存在着博杂化的倾向。如明末学者邱一敬、陈际泰,均读书很多,堪称博学。他们的学问,邱一敬有“三河杂货行”之称,陈际泰有“广城杂货行”之号。两人学问的共同之处就是如同“杂货行”一般的博杂,应有尽有,所不同者只是多少而已。在知识构成上,博杂不等同于博雅。正是在这一点上,明儒与清儒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明人学问,博而杂,甚至“博而不精”;而清儒学问,尤其是乾嘉学者,正好能做到博而精。
尽管明人学问存在着博杂的偏弊,但无疑是文化多样性的一种表征。在文化趋于多样性的大势下,明代的知识人开始对“异端”加以重新的认知与包容,甚至不再排斥“异端”。如王阳明对“异端”有其独特的看法,认为“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为异端”。以愚夫愚妇或百姓日用作为区隔“同德”与“异端”的标准,这是明代文化多元化的典型例证,其结果则是不再贬斥异端,甚至对佛老不加排斥。
晚明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思想家之间争辩不休,文化呈现出多元纷呈的面貌,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作者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