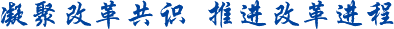理性官僚制建构与中国行政文化转型
发稿时间:2016-12-29 13:38:01 来源: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作者:李韬 吴思红
作者简介:李韬,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地方政府学。武汉 430079;吴思红,杭州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农村政治。 杭州 310024
内容提要: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专业化分工、等级制、法理化规则的遵从和非人格化”的基本要求,中国理性官僚制建构表现出严重的不足。这不仅导致了科层组织的运行效率低下和腐败行为,而且滋养了“官本位”、“家长制”和依附行为取向等传统行政文化的生长和续存。所以,在理性官僚制、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逻辑关系上,虽然传统行政文化对理性官僚制建构有一定的反作用,但理性官僚制的建构才是决定传统行政文化的续存和生长的主要因素,进而决定着行政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当前中国行政文化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在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前提下加强理性官僚制的建构,完善公平竞争的干部选拔制度与功绩制;同时要加强契约法治精神和人本(人格平等)精神等现代行政文化价值的引导。
关 键 词:官僚制/行政文化/制度建构/法治
自从马克斯·韦伯提出官僚制以来,人们更多地关注理性官僚制类型的适应性和实际效能。从20世纪到现在,对理性官僚制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组织运行的刻板性和适应性以及技术要求的理想性上。这是因为,一方面实然上的官僚制往往因人性因素和非正式关系的影响而难以达到理性程度,另一方面过度程式化的组织运行规则不仅增加组织运行成本,而且降低组织对环境的适应性和运行效率,[1](PP8-11)进而难以适应新公共管理运动背景下的市场化进程,所以新公共管理理论要把理性官僚制放到政府与市场关系上予以改造。[2]但是,对于中国行政组织而言,由于政府管理体制特别是政治权力结构因素的影响,官僚制建构根本没有达到理性的基本要求,表现出在非人格化制度建构上的严重不足。这不仅导致了公共行政组织的运行效率低下和大量腐败行为,而且滋养了“官本位”、“家长制”、关系主义等等传统行政文化因素的续存和生长。所以,在理性官僚制、传统行政文化、现代行政文化的基本逻辑关系上,理性官僚制的建构决定着传统行政文化的续存和生长,进而决定了行政文化现代化:而传统行政文化只是对理性官僚制建构起着一定的反作用。本文试图在探索理性官僚制和当前中国行政文化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分析理性官僚制不足与传统行政文化续存的内在逻辑关系,提出理性官僚制建构和促使传统行政文化向现代法治契约型文化转型的基本路径和方法。
一、理性官僚制和中国行政文化的基本特征
理性官僚制是指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具有专业化功能和固定规章制度、设科分层的组织管理形式。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三种不同的统治类型,即传统型统治、个人魅力型统治(卡里斯玛)和法理型统治。这三种统治类型分别对应传统型权威、个人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他认为,传统型权威在“父权家长制”(如皇权)里得到典型的表现;魅力型权威是建立在个人不用理性和不用传统阐明理由的权威之上的类型,是一种人格感召型权威;而法理型权威来源于一种制订为章程的理性的规则之中,这些规则作为有普遍拘束力的准则得到服从。如果根据规则对此负有使命的人要求服从的话,这时,命令权力的体现者个人是通过理性的规则体系合法化的,而且只要他的权力实施符合那些规则,那么它是合法的。服从的是规则,而不是个人。所以,这样作为一种统治实体的理性社会化了的共同体行为,以法理型权威为基础的现代官僚制,是纯粹而理性的类型。[3](PP277-278)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定义,理性官僚制有如下特征:第一,专业化分工。为了实现组织目标,必须通过法律或者行政规则对官僚制统治机构进行固定的分工和权限的确定,分配相应的义务和行使权利,并招聘具有一定普遍规定的资格人员。在韦伯的分工体系中,人的差别只有技术能力的差别,而不再是身份和社会差别。所以,组织成员的选拔,必须采用公开竞争诸如考试的方式。第二,等级制。官员之间的从属关系是由严格的职务或者任务等级序列所决定的,从上而下的等级序列安排中存在制度化的审级制,即上级监督下级。但是,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并非等同于上级机构可以随意包揽下级的事务或者越俎代庖。换言之,每一个职位上的官员都有着明确而具体的权力范围,每个职位上的官员都应该照章办事而不至于越出其职权范围。所以这种等级制不同于以往传统性权威按人格身份所形成的等级结构,而是按组织法定权力形成的。这种结构摆脱了对人身的依附,其实质是专业技术和知识差异,是一种制度而不是身份赋予的等级权力。[3](PP278-280)第三,法理化规则的遵从。官僚制组织的构建、部门分工、职位设置、成员选拔、组织成员的权力和责任的赋予,都是由相关的法律制度明确规定。以“法治”代替“人治”,以“遵从制度替代人身依附”,以“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所以,官僚组织从实质上讲是一种高效执行的工具,而不是带有社会情感的组织载体。第四,非人格化。非人格化是指在官僚制组织中排斥个人魅力,组织运行不受感情影响。换言之,职业官僚只服从法律制度而接受上级的指挥和命令,而不是直接服从站在高层级的命令者本人及其人格魅力的召唤,或者是服从附着在其身上的身份地位,更不是服从由传统习俗决定的社会等级。这就改变了传统社会中的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与个人忠诚关系。所以,只要官员的工作和利益不是由其上司个人的好恶所决定,而是取决于制度化的程度,即把他的工作经验、年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等等都加以量化,那么,个人的服从对象就不再是拥有特定职务的个人,而是个人拥有的特定职务,或者说为一个非人格化的组织和组织目标服务。[4]
由此可见,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撇开了人的情感和文化因素,确实存在一定理想主义成份,但其目的就是要以法理化、专业化和非人格化的组织建构排斥和消除传统型和个人魅力型权威所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依附型行政文化,这就是推动传统行政文化向现代行政文化转型的关键和原动力。
行政文化是指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所应共同信守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人群关系及价值观念。[5](P292)其中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的行为模式、人际关系和与此相关的行政意识等是本文的核心内涵。
一些学者认为,当代中国行政文化具有现代性的外层和传统性的内层结构并存的二元性特征。这是因为当代中国官僚制脱胎于马克斯·韦伯所称的“传统型”的官僚制结构,其内核并没有脱离严密的等级集权制和依附关系。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断促使传统型官僚制结构解构,但对照现代官僚制精神,中国行政组织文化仍然存在诸多非理性因素。[6]
与传统型或者个人魅力型权威相对应,当代中国行政文化具有典型的非理性的依附性文化特点,未能与现代法治精神和市场经济相一致,具有明显的转型滞后性。人们更多地把这种落后的依附文化归因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传统儒家文化一味强调治国者自身抽象的品德和修养,[7]把道德的社会调节作用扩展到解决政治社会关系上,如君与臣、君与民、臣与民、民与民等,使其成为行政管理的中枢和力源,[8]由此产生了“人治”向“法治”转变的困境。所以众多学者认为,正是这种“人治”道德教化和人伦宗法文化的传承,造就了当代中国特殊主义的行政文化,其传统性和落后性十分明显。
首先,人格依附取向。在行政组织体系中,人格化权威的服从关系代替了法理化的制度权威关系,换言之,个人服从的是掌握权力资源的人,而不是由制度赋予的职位,把职位与职位、事与事之间的关系代换为人与人的关系,由此形成唯上是从、马首是瞻、看人说话和因人办事等普遍性的行为取向。所以在这种组织文化背景下掌握权力资源的领导者往往通过权力运作以增加自身的魅力型权威,减少组织中的法理型权威,进而强化下级对上级的依附性。这种依附关系中,普遍信任总体下降,人与人的交往变得小心谨慎。特殊信任往往只是存在少数人之间,特别是领导者与身边的人,或者与有亲缘关系的人之间。
其次,“家长制”和“官本位”思想。“家长制”和“官本位”思想是传统中国“家国同构”的政治产物。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中,人们不仅潜意识地认同高高在上集权威于一身的皇帝,而且认同形形色色的族长、家长等,对权威畏惧、崇拜与依附,并内化为行政人格。这就导致在当代官僚体系中,一方面一些掌权者往往得势后就会盛气凌人,唯我独尊,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另一方面普通成员往往阳奉阴违、拍马逢迎、诌媚阿谀、权欲熏心。这种依附权威与自我中心的奇妙结合,构成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又一奇妙的官本位特征。[9]与此同时,由于人们将家族制度上升为社会伦理,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和处理人际关系,形成“泛家族化”历程①。所以在“官本位”意识和“家长制”的作用下,“人治”、“忠君”、“依附”和“关系主义”等构成了中国当代社会和政治体系中的普遍生态。
再次,法治理念薄弱。在“人治”、“忠君”和“依附”的政治生态中,由于法制建设滞后、法治精神和行政伦理不足,人们只是依附行政组织中掌握权力资源的人,而不是依靠和遵从法律制度。他们没有独立人格的尊严,只是家丁奴仆,把下属对于上级的尊敬和服从常常与私人关系混为一谈,以私人关系代替法律制度权威关系。所以在官僚组织中“人情风”盛行,权力拥有者在升迁、晋级和工作变动等方面违背原则,搞裙带关系。[7]
由此可见,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人们更多地把中国行政文化的落后性归因于传统文化和宗法关系的影响,或者说在逻辑上理解为,传统的“人治”依附文化和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阻碍了现代法治—契约型的行政文化发展。而按照这样的逻辑进路,就会得出这样的判断:要推进中国行政文化现代化,就要首先消除传统的“人治”文化和由此形成的关系主义,进而才能推进现代理性官僚制建构。这意味着消除传统的“人治”依附文化和由此形成的关系主义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意味着行政文化现代化和理性官僚制的建构更具有长期性。
二、作用与反作用:理性官僚制建构的不足与传统行政文化的续存
如果我们从文化—制度—利益—行为的视角来考量当前中国行政文化落后性的话,就会发现以上主流观点过于夸大了传统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对当代中国行政文化转型和理性官僚制建构的影响。事实上,虽然传统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对当代中国行政文化转型产生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对行政文化现代化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行政文化的载体:理性官僚制本身。理性官僚制建构对中国行政文化转型起着主导作用,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对理性官僚制建构和行政文化现代化起反作用,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续存的实质就是理性官僚制建构不足的问题。
按照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现代理性官僚制的专业化、等级制、法理化规则的遵从和非人格化等要求,当代中国理性官僚制建构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专业化、非人格化与法理化规则的遵从上。这种非人格化与正式规则的使用,以及基于技术能力的人员选拔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正如唐斯指出的那样,当个体官员的决策制度受到正式规则的限制时,社会等级、财富、裙带关系或者其他个人特点就很难对官员的决策产生影响。这样,人员的雇佣、留职和提升就会基于技术资格的基础,而不是这些人的某种关系资源,或者具有决策权的官员意愿。[10](P69)
当代中国官僚组织中专业化不足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领导者的非专业化或者专业化不足上。比如农业局或农委的正副职领导可能来自于宣传部门,非科班出身而缺乏农业生产管理的专业知识;城市建设局的正副职领导可能来自于组织部门,非相关专业出身而缺乏城市建设规划知识;教育委员会主任可能来自于乡镇府,非相关专业出身而缺乏专门的教育管理知识。在官僚制组织内部的某个职位安排上同样会出现类似情况,一个有专业背景要求的处长职位可能由非专业化或者专业化程度不高的人员所担当,一个十分专业的人员往往被排除在管理岗位之外。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不是当前干部人事制度缺乏专业化取向,也不是组织体系中缺乏专业化人才,而是官僚组织中法理化程度不高所导致的专业化取向偏离。虽然在当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相关的组织管理制度中有明确的专业化和管理能力要求,并在形式上有较为完整的规范性选拔程序,但由于制度条文弹性较大,在具体应用中领导者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所以领导者在实质上掌握着下级干部和一个普通成员的评价权、定岗权、职务晋升的最终决定权以及相关的处罚权。也就意味着领导说了算,其权力很少受到组织运行中相关制度的约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偏好选拔谁,任用谁,处罚谁,甚至于在人格上抬举谁。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内部就会形成自上而下的权力和利益的依附关系(clientelism),这种关系当然不是建立在制度遵从和非人格化之上的等级关系,而是人格化等级控制关系。
所谓依附关系是指“恩庇—依随”二元关系,在此关系中恩庇者和依随者之间在多数情况下形成一种工具性友谊,其中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庇护者使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被庇护者提供保护和利益,而被庇护者向庇护者提供一般性的支持和帮助(包括个人服务)以作为回报(斯科特)。[11]这种关系广泛存在于既存政治社会体系中,是一种不平等权力地位的行动者间的非正式特殊互惠关系,其中恩庇者具有较高的权力地位,依附者透过对恩庇者的效忠与服从来换取生活所需的资源(卡夫曼)。[12](P109)这一庇护结构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不平等的互惠性。庇护者运用自身所拥有的权力资源与被庇护者进行一种不对等的物品或者服务交换,较低地位的被庇护者得到那些有助于自己缓解来自于环境威胁的物资和服务,而较高地位的庇护者获得诸如个人服务、尊重、服从、忠诚,或者一种具有政治性质的支持如投票的回报。[13]二是工具性。这种庇护和被庇护的关系与纯粹的情感或者忠诚不同,是权力资源不平等所形成的交换关系,换言之,那些在表面上看来的信任与忠诚、情感与认同、尊重与服从等主要来自于在不平等的交换,在多数情况下这种交换往往先于情感或认同的形成,或者说交换是情感和认同的基础。三是特殊主义。恩惠施予或回报的对象是与其有特殊联系的个体,而非普遍的水平群体。庇护—被庇护的单一联系可以扩展为群簇和金字塔。庇护簇即一个庇护人与其直接追随者的集合,庇护簇扩大但仍集中于单一庇护人则形成金字塔。[14]
在当代中国的官僚制组织结构中,由于这一庇护关系的普遍存在,一些领导者往往倾向于选择“家长制”模式来实施组织管理,这样既可以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不断满足个人权威需求和强化下属的依从性,又可以获得较高的管理成效。所以领导者在选拔干部或者某个重要岗位的人事安排上更可能把忠心和顺从性作为人品的道德范畴予以首要考量,然后把能力或者专业化因素置于其次考量的位置。而作为道德范畴的人品虽然包含有正派、诚实和宽厚以及遵守制度等等因素,但由于缺乏有效的人品评价办法,所以领导者往往把忠心和顺从性看成人品好坏的全部,甚至于纳入政治思想范畴。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被领导者或者下级为了得到领导者的认同和赏识。除了要做好本职工作,关键还要正确把握领导的首要价值选择和需求,即忠心和顺从,为领导所想,始终与其保持一致性。即使领导的思想和行为有错或者有悖于制度规范,也要紧跟其后并维护领导的权威,这样才有可能成为领导的资源交换的对象。
由此可见,这是一种“人治”的权力依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领导说了算的决定权构成下级对上级依附的基础。换言之,如果组织资源是通过制度化权威进行分配的话,那么被领导者就不会产生依附上级的动力,上级领导也就不会拥有“家长制”作风的资本,“官本位”思想和“人治”依附文化就会失去生长的土壤,“关系主义”就会减弱,能力和专业化价值就会产生引导作用而得到充分的表现。所以官僚制组织中资源分配管理制度特别是干部选拔制度的不够完善,领导者对组织人事管理的有效控制,既是理性官僚制不足的主要表现,又是落后的传统行政文化续存的总根源。
然而,在认识理性官僚制建构不足所导致的传统行政文化续存总根源时,也必须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及其所形成的社会交往结构对理性官僚制建构和行政文化现代化的反作用。换言之,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基础的非正式关系广泛地侵入了正式组织或科层制体系并阻碍理性官僚制的进程和行政文化现代化。[15]在中国,以宗法制为基础的血缘关系和伦理规则渗透到官僚组织中,重血缘亲情的行为取向必然造成一种偏私和势利心态,人与人相处缺乏普遍原则和一致的标准,看人情办事成为一种常态。[9]这是一种工具化的社会交往结构,并以“差序格局”出现,即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处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6](P25)在这种“差序”关系结构中,作为官僚组织的下级或者被管理者总是倾向于通过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对领导者进行投入(送礼物、对领导者工作上的支持和领导人格上的尊重以及权威的维护)并成为领导者圈内的人。投入越多,越能进入领导圈内的核心,也就越能得到领导的信任,获取资源交换的可能性越大。同样,作为领导者一般倾向于与身边亲近的人进行组织资源交换。这是因为一方面领导者对身边的人有更多的了解和信任,虽然这种信任有可能更多基于利益交换所形成的特殊信任或者表面上的价值认同信任,但是相比较于外层的人而言,这种信任可能更可靠;另一方面在身边的人对其投入的过程中,相互之间也有可能产生一定的情感,作为领导者往往基于这种情感或者互惠“面子”就会优先选择性地对自己身边的人给予回报。虽然这种投入和回报在表面上呈现出“亲亲”、“尊尊”和“不亲”、“不尊”的个人道德“修养”,但掩盖了其中自私的本质,同时也抹杀了待人处世的公正品德,助长了当代中国官僚制中的关系主义,腐蚀了官僚体制的理性基础,[9]进而阻碍了行政文化现代化。
不过,必须指出的,虽然这种由传统文化所构建的社会交往结构(非正式关系)能够广泛地侵入官僚制体系,但是其存在的基础仍然没有脱离领导者所掌握的组织资源以及可能利用这些资源与下属交换利益的条件。这意味着正式规则给予了领导者充分的包括干部选拔在内的资源控制权;或者正式规则不能涵盖所有的自由裁量权;或者规则本身存在的漏洞等,由此造成领导者的权力游离在规则之外。[10](P69)所以传统文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交往结构对理性官僚制建构所产生的反作用在本质上是由官僚制的理性程度所决定的。理性官僚制建构越充分,这种反作用越小。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行政文化转型必须着力推进理性官僚制建构。
三、理性官僚制建构与行政文化转型
树立和强化现代行政文化价值引导,推进理性官僚制的建构,是现实中国行政文化转型的根本出路。理性官僚制建构主要是完善公平竞争的干部选拔(含非领导职务晋升)制度和功绩制。
现代官僚制中的行政文化价值主要包含有契约和法治、人本(人格平等)精神以及由此构成的关系结构。本文的契约精神是指官僚组织成员之间在自由、平等和守信的基础上尊重规则的普遍意识;而法治精神指追求法治的价值取向,以及实现法治或良法善治的理想、信仰和思想原则,包含法律至上和人民意志至上。追求良法善治的法治精神包含有民主自由和尊重保障人权精神、公平正义精神、公正司法精神、监督制约公权力等。[17]契约精神是法治的灵魂,法治是契约精神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延伸和应用,也是契约规则执行的重要保障。在官僚制组织中,无论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都应该树立法律至上和规则至上的观念,以法治和规则来调整和约束自身的行为,依法依规从事组织管理活动。同时摒弃和排斥人治思想、王权主义、宗法观念、官本位意识和臣民意识等。人本精神就是指在法治和规则之下官僚制组织成员的人格平等意识。换言之,上下级之间不应该以内部迷信、崇拜个人权威而形成依持—恩庇关系,而是一种契约化的服从关系与人格平等的人际关系。虽然在官僚组织中职位和权力呈现自下而上的不平等,以及由此形成非人格化的权威服从,但在人格上应该是平等和独立的。这种人格的平等和独立性以及制度的权威性是解构官僚组织中家长制和宗法关系主义的关键。
在塑造和树立以上现代行政文化价值过程中,领导者的示范和引导是十分重要的。正如库珀指出的,领导者的个人偏好和价值取向以及管理方法等对组织文化具有重要影响,他们如同“潜在的杠杆”,激励或者阻碍负责任行为的产生。换言之,如果领导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做出行动,并做到表里如一,那么组织文化和领导权威就会产生正面效应,否则,领导权威不仅会削弱,而且会腐蚀下属的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18]这就要求领导者有良好的专业素质、能力水平和品德修养,同时也要有完善的制度规范约束领导者的权力运行。实践表明,拥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能力水平以及良好品德的领导者,更有可能遵从制度规则和实施法理型权威的人性化管理,减少家长式作风以及由此产生的裙带依附关系的影响。特别在官僚组织中有良好的制度规范和约束的情况下,领导者更能自觉地成为现代行政文化的推动者和主导者。所以作为理性官僚制建构的重要内容,公平竞争的干部选拔(含非领导职务晋升)制度和功绩制既是选拔能力品行优良领导者的根本保证,又是促使领导带头示范和引导现代文化价值的前提和塑造现代行政文化价值的基石。
在当前官僚制组织运行中干部选拔制度的完善要注重解决专业化门槛设置和公开竞争机制等问题。首先,推进专业化门槛设置的规范化。专业化门槛是指干部选拔中职位公开竞争的入门专业化标准,一般包括学历、专业、技术职称和从事专业的经历。当前现代官僚制组织专业化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专业人才短缺、学习型组织建构不足、专业化门槛设置缺乏刚性制度约束而导致专业化人员难以进入领导职位等,其中专业化门槛设置缺乏刚性的制度约束是主要原因。在当前的干部选拔制度中虽然有“专业化”和基本“学历”等要求,但只是作一般性的抽象描述,未能对具体职位门槛做出诸如“国民教育本科学历”、“某某专业”等等更为定性定量化规定,由此导致自由裁量权的外溢,领导者可以利用这一自由裁量权外溢为自己喜欢的人“量身订做”门槛标准。比如一个有专业文字功底和正规本科或者研究生学历要求的职位门槛可以降到继续学习的专科学历或者非正式的学历门槛水准;一个有工作经历或者某一背景要求的职位门槛标准可以降到零标准。不仅如此,领导者也可以通过某种门槛设置比如身份(公务员和事业身份)、工作经历、年龄等等把有竞争力的专业化人员排除在外,避免自己的人在竞争中落选,从而实现自己的人事意图。在现行干部选拔制度中专业化门槛设置不规范、缺乏刚性的制度约束,不仅造成了干部群体的专业化不足,而且导致官僚组织中的专业化价值引导力降低和依附性的强化。所以必须在国家层面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对官僚制组织特别是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官僚制组织的竞争性选拔门槛进行规范化和专业化设置,减少领导的自由裁量权,消除其中的漏洞,由此促进官僚制的专业化。
其次,要推进公开竞争。公开竞争不仅可以促进组织成员的专业化,而且可以促进官僚组织中的公平价值文化的成长和组织凝聚力。在干部选拔(包括非领导职务)中应该遵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实行公开竞争的方式选拔任用干部。当前公开竞争选拔干部的方式已实施多年,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然存在一些环节上的机制缺陷,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在竞争资格设定上领导的决定权过大。比如在一个既有公务员又有事业身份的单位中,领导可以设定公务员身份门槛而把有竞争力的事业身份的人员排除在外;也可以根据资历、专业或者其他附加条件把选拔的范围缩小到自己圈内之人中。这样就会导致选拔的范围过小和后续竞争性程序失效。二是笔试面试缺乏规范化(试题保密、程序公开透明)和科学性(考试内容的针对性和区分度),由此造成笔试面试选优功能下降,能力水平区分度不够。三是组织考核形式化。由于关系主义和“德能勤绩廉”评价标准虚化以及考核程序的形式化(领导有最终的话语权)影响,[19]评价人一般只说好话而不说真话,所以组织考核的意义有限。以上三个方面的机制缺陷不仅减弱了“赛马”选人的实际效用,而且反过来强化组织领导在选人用人上的权力和人格化的依附性。所以要从实质上有效推进公平、公开竞争和择优选人机制建设,实现“赛马”选人的目标,就必须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进一步细化竞争性选拔环节上的程序,减小或者清除领导在竞争资格与考核上的自由裁量权以及全过程的控制权。同时要引入专业化的第三方考试、评价机制,以此增强笔试面试的针对性和公平性,进而提高参与竞争人员的能力区分度。
功绩制是指干部选拔和组织内部成员职务晋升基于能力和业绩的制度,换言之,就是以个人的工作实绩和贡献大小决定其职务的高低和工资待遇的多少。功绩制的功能主要有激励和引导作用,一方面通过奖勤罚懒的激励,提高组织运行效率,另一方面引导组织成员简约人际关系,减弱和消除组织体系中的依附文化和投机氛围。即使功绩制在官僚制的实际运用中无法摆脱复杂人性因素的影响和无缝隙制度建构的困境,而遭受后现代理论的批判,但对于当前现代理性官僚制建构严重不足的中国来说,功绩制建构仍然是理性官僚制建构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20]然而,功绩制必须依托有效的绩效评估制度才能产生作用。当前我国官僚制组织的绩效评估制度仍然存在形式主义和低效率运作的问题,其影响因素很复杂。一是缺乏工作职位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未能有效地描述工作难度(技术水平)和工作任务的大小,在考核过程中缺乏具体的可比性示标而无法区分成员之间绩效的好与坏,高与低。二是中国是“熟人”社会,同事之间相互给“面子”,谁也不愿说真话而得罪日日相见的对方,即使是领导也不愿或者不敢触动多数人的利益而把各职位分出一个高低,包括领导在内的多数人都接受抽象的“德能勤绩廉”自评、互评、组织评和领导终评的通用办法。三是由于职位性质的多样性和工作难度以及工作量的差异性影响,建立一个公平有效的评价体系往往会遭遇到高成本和费时的矛盾,由此导致绩效评估制度建设一直难以获得突破性进展。所以,纵观以上因素的影响,绩效评估制度建设的关键就是高层领导的重视和官僚组织体系中主要领导的担当精神与决心。这就要求从上至下形成合力不断推动基层组织体系中评估示标的定性定量化建构,领导带头引导和改变一些传统落后的组织文化,在绩效评估工作中下真功夫,逐步提高绩效评估的效率和效价水平。
理性官僚制与法理型权威的形成基础即民主法治是统一的。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权力制约和监督,就不会改变“人治”的格局,理性官僚制建构就会陷入困境,行政文化现代化就会止步,所以理性官僚制建构和行政文化现代化必须以民主法治建设为前提。同时,理性官僚建构可能遭遇到一定历史时期政治权力结构的制约,表现出权力结构上的悖论,一方面国家需要自上而下的人格化官僚制来维持政治秩序和国家管理,另一方面理性官僚制建构也会裂解自上而下的权力链条,造成国家管理秩序的混乱甚至政治不稳定,由此造成理性官僚制建构和行政文化现代化的限度和困境。所以,理性官僚制建构和行政文化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推进的系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要防止以传统文化和某些客观因素为借口阻碍理性官僚制的建构和行政文化现代化的行为,又要防止不顾客观条件的冒进的思想,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理性官僚制的建构和行政文化现代化。
注释:
①泛家族化指把地缘、业缘、学缘以及有利益互惠关系的“外人”内化为可以信任的“自家人”。
参考文献:
[1][英]戴维·毕瑟姆.官僚制[M].韩志明,张毅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2]何显明.现代理性官僚制的理性审视[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4(1).
[3][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张康之.韦伯官僚制合理性设计的悖论[J].江苏社科学,2001(2).
[5]张金鉴.行政学新论[M].台北:三民书局,1982.
[6]范绍庆.官僚制精神与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J].行政论坛,2005(1).
[7]时和兴.当代中国行政文化的特点及其走向[J].南京社会科学,1994(4).
[8]王文耀.周代的“德”和“德治”——兼论“德治”的历史影响[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6).
[9]陈尤文.中国行政文化流变及其特征[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3(4).
[10][美]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M].郭小聪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1]James C Scott.Patron-Client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Southeast Asia 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72,66(1):91-113.
[12]Robert R.Kaufmun."Corporatism,Clientelism,and Partisan Conflict:A Study of Seve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in James M.Malloy,ed.,Authoritarianism and Corporatism in Latin America.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9.pp109.
[13]John Duncan Powell.Peasant Society and Clientelist Politic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0,64(2):411-425.
[14]张立鹏.庇护关系:一个社会政治的概念模式[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3).
[15]纪莺莺.文化、制度与结构:中国社会关系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2(2).
[16]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17]高强振.论法治精神的逻辑内涵和外延[J].贵州社会科学,2009(5).
[18]Terry L.Cooper.Exemplary Public Administrators:Character and Leadership in Government,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92:28-29.转引自刘召.库珀行政伦理理论初探[J].道德与文明,2010(1).
[19]曹桂芝.“买官卖官”背后的选人用人制度漏洞探析[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