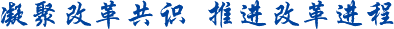财税改革与经济繁荣
发稿时间:2013-12-03 00:00:00 来源:腾讯文化 作者:李炜光、秦晖、于建嵘
2013年11月27日,腾讯网十周年“中国说”思享会在北京举行。财税学者李炜光、历史学者秦晖、社会学学者于建嵘以及纪录片导演李成才共同参加了第一场题为“财税改革与经济繁荣”的分论坛,活动由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冯兴元主持。在谈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财税改革时,李炜光表示,全会提出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问题其实就是指分税制的进一步完善和改革,而这个改革的重点在于以法律确定各级政府的公共职责。李成才认为财税改革事关商业繁荣、意识形态甚至是国家的建立,所以他要用纪录片的方式向国民传播西方先进的财税观念和制度。秦晖指出,中国的财税问题与西方截然相反,政府的收税能力太强,所负的责任又太小,因此财税改革的关键是要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并落实政府的责任。于建嵘在谈到这次三中全会时,认为政府没有出台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路径,他接着前面关于落实政府责任的话题进一步指出,问责政府要依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有制度性的问责才能保障纳税人的权利。下面是文字实录:
李炜光:税制改革的核心是财权与事权相匹配
冯兴元(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女士们、先生们,这个分论坛的主题是财政,刚才大会组织已经讲到了,中国存在分权、集权的治乱循环,这次三中全会能否打破治乱循环?能否形成比较好的真正的分税种的体制?这里面有不同领域的专家,李炜光教授是天津财政大学的首席教授,首屈一指的财政专家。秦晖老师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于建嵘先生是赫赫有名的维权专家,中国是维稳大国,他是维权大家。还有我们赫赫有名的李成才导演。既然是财政的题目,先请李炜光教授讲讲“分税制何去何从”,地方财税体制有什么问题,三中全会在这方面有什么新突破。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教授):这次三中全会特别提出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谈的其实就是分税制。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分税制是在1994年制定并推出的,当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分权,而是解决“两个比重”过低的问题:一个是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过低。二是财政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过低。邓小平时代采取的一个主要政策是放权让利,它的结果是穷了中央、富了地方。这种情况跟我们单一制体制形成了矛盾,使得中央在职能的履行方面发生了问题。所以分税制主要是为了改变中央的财政困难,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重新划定各自的事权和财权。这个目的很快就达到了,中央和地方占有财政资源的比重发生了颠倒性的变化。分税制改革终结了这个政策。
显然,分税制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央地分权上,虽然保证了中央对财权和财力的拥有,重新保证了中央集权的财政需要,但先天不足的问题暴露出来了,这几年问题越来越严重,主要表现在财政秩序的紊乱。中央财政收入有了充分保证,但造成年终花钱的问题,在财政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存在错配的问题。最重要的还不是中央,而是地方,越是基层政府,财政资源越稀缺,越困难,这就必然导致地方政府突破现有的制度框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融资的行为发生。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贴近于民众最近的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都需要财政资源。但我们的财政体制是往上集中,越到下面越困难,使基层政府在履行公共职能上缺少财力的保障。还有一个问题,这些年倡导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让公众更多地参与到预算、财政等公共事务中来。可你的财政体制是往上集中,下面能决定的事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能参与什么?能决定什么?这也是一个体制问题所造成的问题,因此出现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同时民主政治推进也需要财政的保障。所以我们的财政体制、分税制应该进行改革。
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了十几年,大家看到中央和地方处理他们之间的财权、财力的问题时,缺少法治。我们国家有十八个税种,大部分未经过正式的立法程序,但至少在财权关系上还有一些成文的法规、规则,,但中央和地方、地方以下各级政府在处理他们之间的事权关系时,却很难找到这种规则,甚至连条例之类的法规都没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财税学界经常争论的是财权和事权匹配的问题,中央这次没有用这个词,它用的是“支出责任和事权相适应”,没有用“匹配”,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说明我们原来争来争去的问题可能是个伪问题。最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公共责任、支出责任不明确,支出责任不明确,该做什么事都不明白,财力的配置怎么会不出问题?所以这次分税制改革最重要的是要把各级政府的公共责任用法律确定下来,而财力配置本身则是个相对简单的技术问题。
于建嵘: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政策依然空缺
冯兴元:李炜光讲到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包括整个财政体制的法治化非常重要,这里面于建嵘教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现在新一轮的改革要点里面有没有涉及到财税体制改革的因素,会否打破土地财政的格局?维稳格局?会否终结土地的开发循环?
于建嵘(社会学学者,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土地财政问题很复杂,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城镇化发展进程提得很高。可今天的地方没有这样的资源。今天的问题是没有资源时怎么办?要搞政治怎么办?两个办法:一是挪用农村已有的资源,今天开会时有官员说要把所有的资源集中使用,农村发展本身就有问题了。第二还是土地,为什么十八大后,农村的土地问题,包括强拆强建的问题为什么更加严重?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农村土地发生争议时,解决的路径仍然没有。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不会有太明显的改变。
李成才:税收问题关系到商业繁荣、意识形态甚至国家的建立
冯兴元:李导演是唯一一个来自于文娱界的嘉宾。我有跟商业有关的问题问你:财税改革如何影响商业?这一轮财税改革怎么影响到企业家、业界?房产税要加征、个人所得税要更严格的征收,还有企业所得税这方面也有一些改革的举措,财税改革怎么影响商业?
李成才(纪录片导演):我是一个导演,只是拍这类纪录片比较多,不管是《大国崛起》还是《华尔街》,尤其是拍《货币》时,我们搞了一次座谈会,谈到国家关系、权利关系是怎么一回事。后来税务总局让我们拍一个有关世界范围内的税是怎么起源的片子。
回到问题,财税改革是否会影响商业繁荣?这个事说小也小,说大也大,肯定会有很大关系,以我拍摄过的例子做说明。
第一,财税问题不仅仅是对商业繁荣,与国家形态、秩序也联系在一起。美国革命的第一枪在1775年打响,1776年就推出了《独立宣言》,仅仅一年的时间。革命开始一年多后,当人们开始有诉求想表达时,出现了潘恩的《常识》。这本书讲到,你这些权利真要想实现的话,如英国所说的无代表不纳税,必须要有一个国家。所以在殖民地很快就建立起了这样的国家。税收问题简单说和经济繁荣直接挂钩。现在有人说国家要宏观调控,就做这样一件事,经济就能够繁荣。
第二,如果将来要增加税收,我是纪录片导演,不是电视剧导演,也不是电影导演,他们可能比我更着急,因为他们比我挣钱多。但我相信,一旦人们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的话,他们一定会设法逃税和避税。我希望将来能拍一部税收的片子,讲税和国家、社会组织、社会秩序的关系,给全国人民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我是一个老媒体工作人,90年代的时候连“纳税人”这个词还不能提,这是从我的角度来回答主持人的问题。谢谢大家!
冯兴元:你回答得很好,你把税收、低税模式的重要性讲得言简意赅。你把财税体制改革跟商业繁荣的关系讲完后,又讲到它会影响到大国的崛起,大国崛起的途径是低税模式,而且涉及到纳税人的权利。那我们新一轮改革方案里有没有提到改善纳税人权利的说法?有没有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未来?下面有请秦晖老师来谈一谈。
秦晖:财税改革应该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并落实政府的责任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关于法治、财税,大家期望很大。我觉得财税改革的背后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后者限制了中国财税改革发展的路径。自古以来,我国的财税问题就是为朝廷开源节流,一方面想办法多收税,从农民那里多征税,另一方面想办法花得少,所谓花得少是给老百姓花得少。这种思路和现代国家的财税改革不是一回事。现在民主国家,财税问题说得简单点就是政府负债问题,1928年到现在愈演愈烈的就是债务危机,2008年危机到欧洲成了主权债务危机,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简单说就是向老百姓收钱,但老百姓掐得很死,但老百姓又逼得你不得不花钱,于是就有了政府债务问题。如果把这样的思路套到中国来,认为中国所谓的财税改革也是要以解决政府所谓的债务危机,那就彻头彻尾的错了。因为在中国的体制下,严格来说,本来就不会产生这种问题。皇上要跟老百姓收税,想收多少就收多少,给老百姓花一分钱就是皇恩浩荡,我不给你就不给你,你也不能跟我要,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有政府债务?所以我觉得,中国出现政府债务问题,那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方面饿死了几千万人,另一方面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什么税都没有的情况。当然不会有债!想横征暴敛就就横征暴敛,想一毛不拔就一毛不拔,怎么可能有债?现在政府想向老百姓拿钱比以前更难,老百姓又逼它花钱,而且比以前逼得更狠,我觉得这是中国莫大的进步。
我觉得要有财税改革,整个思路要有变化。不能仅仅从朝廷的钱袋子出发,从为朝廷开源节流的方式去考虑。通过开源节流使政府有很多的盈馀或者更好的债务,这是不对的。尽管这可能是现代国家的方式,比如西方的财税改革就以这个为核心。但是我们和西方的问题截然相反。我们的问题不是政府征税的能力不够,而是太大了,我们的问题也不是政府的责任太大,而是太小了。现在世界上最奇怪的现象是,我们国家拥有社会主义的权力,严格说是超社会主义的权力,但只愿承担资本主义的责任,甚至连资本主义的责任都不愿承担。西方国家是有限政府,只有资本主义的权力,但老百姓要求他承担社会主义的责任,甚至共产主义的责任。福利国家严格说是共产分配,也就是按需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所以产生了很大问题:既要马儿跑又不要马儿吃草。中国也产生了大问题,但和西方本质上不同,因此解决方案也完全不一样。中国财税改革具体到财政问题,我赞成减税,而且赞成增加福利问责,这两者不矛盾,都是针对中国政府,针对中国问题下药。
刚才大家都提到纳税人权利,纳税人权利的反面是收税者的责任。纳税人权利不足,收税者的责任同样是不足的,这是现在的问题。为了捍卫纳税人的权利当然要“无代表不纳税”,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实现的目标。同样收税者的责任也要逐渐增加问责。在这个问题上,三中全会公报出台,我能理解其中的难处。比如在养老问题上,养老改革现在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政府推卸责任,你们要给我干活,我要推迟发放养老金,而且是强制性的。一种是民间的,要搞养老并轨,不能搞双轨制、多轨制,官员养老都是百姓支付的,而且他们来决定老百姓多交费、晚拿钱。现在着手因此强制性推迟退休年龄。当然我理解有关部门在这方面的难度,也理解人处于在不同角色考虑的问题不一样。但我一直觉得解决中国财税问题,一直强调两个原则: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府不能推卸对纳税人的责任。反过来讲,责任不可追问的政府,我们不能让它扩张权力。因此在纳税人权利和收税者责任方面要同时用力,而且这两种主张不矛盾,没有责任的权力是最难限制的权力。
冯兴元:非常精彩,讲到政府问责的重要性,在财政体制方面对政府问责恰恰能够做出很大的贡献,通过财政体制的改革推动问责的实现,李炜教授对这方面有补充的说法吗?
李炜光:纳税人要问政府财政的责
李炜光:问政府的责主要是问公共财政的责。政府财政高度不透明,而且还有资源错配和配置不当的问题。比如孩子们上学路途艰险,需要修一条路或一座桥,但给孩子们配置的资源不到位,这种事情发生了多次,媒体也公布了,让人非常痛心。资源错配的现象非常常见,需要问责。问责首先要公开,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写到了预算透明问题,这是我们希望的一种结果,但前面还有一系列的权利要保障。除了预算要公开,财政资源筹集和配置的信息要公开,而且公开不是摊帐本,把帐本摊给你还是看不懂。美国办各种培训学校和预算展览,香港财政司长每年花两个多月到民间、学校、企业解释他这一年的预算,就是让公众看得懂预算,要理解它,这才是达到问责的要求。而且问责的目的是纠错,我们国家要建立一种纠错机制,公民随时随地可以参与预算过程,参与问责,问责就要有结果。问责是什么?问责主要是问政府财政的责。
冯兴元:好,画龙点睛。前面大家都谈到了纳税人权利,但在三中全会决定里,讲了要赋予农民更多的权利,也就是说现在有很多权利在我的手里扣着,我赋予你更多的权利。这怎么跟问责政府、责任政府联系在一起?怎么维护好农民的权利?
于建嵘:我认为问责最大的问题是谁来问责,李炜光说问责要每个人参与,但没有选票怎么问责?人民代表不是你决定的,而是内部决定的,这个问责是虚假性的,通常需要网民问责。所以我认为问责制度的建立必须在人民代表制度建立的前提下,如果不能对人民代表进行真正的监督,要什么问责?
冯兴元:从国际经验上看,您觉得有什么比较好的问责制,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
李成才:日本是增加税收,到议会倡议、游行。我们最终要解决的有几个问题:为什么要有政府?为什么要交税?交多少合适?我个人不遗余力地做这样的事,所以拍摄这样的影片,是向国人介绍国外的人什么时候拥有了这样的概念。比如美国1775-1787年打仗,这么长时间没有制定宪法,为什么要制定这个宪法?当时是混乱的,都不交税。比如我有10块钱,愿意交1块钱的税收保护9块钱的安全。我们希望我们国家完成这样一种过渡。我本人做这方面的传播工作,希望把国外最基础的东西传播进来,包括这些概念是怎么来的,最后怎么覆盖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公民怎么参与建设等等。我们不能抱怨这个国家没有做或没做好,因为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也是有责任的,我希望能通过做这件事推动社会的进步。
冯兴元:现在有很多新的大片可以看到了,比如说《市场之路》、《问责政府》。
秦晖:人民的幸福不是党和政府的恩赐
秦晖:我们现在讲问责很简单,也就是纳税人对收税人的问责。刚才建嵘讲到没有真正的代议制。没有代议制,制度化的限权问责都是空话。这种努力是使这种制度得以建成的很重要的因素,比如东欧宪政是89年以后才建立,但东欧老百姓对统治者的问责早就开始了。波兰、匈牙利人整天就说葫芦价格为什么贵了、暖气为什么低了两度。而且东欧统治者之所以愿意限制权力,是因为老百姓的无限问责问得他受不了,而且这在代议制之前就实现了。这里面首先要做的是,把汪洋副总理之前讲的一番话予以重视,这个话本来是常识,但中国老百姓都不知道,他在2002年广东省党代会上讲“破除人民的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观念,人民的幸福是他们自己争取来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皇恩晃荡,提供了就要感谢,不提供不能问他要,这样的观念要改变。而且汪洋副总理既然已经改变了,我们老百姓难道还不改变吗?(现场笑)这是很自然的事,所以无论是限权还是问责,这两方面可以做的事很多。
冯兴元:一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符合自然法的精神。
李炜光:美国公民有个体负责的传统。
冯兴元:是不是与三中全会写的权责发生制有关?
李炜光:对,我们现在政府奎及核算用的方法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收付实现制,它最大的缺点是不能准确反映政府债务。权责发生制是西方传进来的,而我们的政府会计核算政府现在还没有使用,这次提出来,我估计会有一个很大的改进。将来编制政府财务报告和资产负债表都用得上。
冯兴元:刚才黄教授提到了“李克强经济学”,实际还有“李克强财政学”,2012年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达到了90%,占GDP的110%,加起来到200%-210%,巨额债务很大。大家负责举债的话,地方政府如何负责?我看到三中全会里没有写地方政府的做法。
于建嵘:没有代议制,制度化的限权问责都是空话
于建嵘:三中全会讲到财政公开,这个公开有两个问题:一是要对人民代表真正进行公开。现在有些地方在做实验,比如在深圳罗湖正在做这个实验,用半年将所有财产进行申报。另外,财政报表很多人看不懂,需要有人告诉我们这是怎么回事。我认为真正的问责的确需要真正的制度性问责,不能只是骂两句。这个我认为是监督,不是问责。监督与问责有区别,问责是能够把它的帽子拿下来,这个问题需要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冯兴元:最后每个人说一句话,对于财税体制改革有什么愿望和顾虑都可以讲。
李成才:我做的是传播工作,希望以我个人的力量普及这方面的知识,让更多人了解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了解我们政府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责任。
秦晖:中国要逐渐落实纳税人的权利和收税人的责任,这两者有了,就有了现代的财税制。
李炜光:这次三中全会提到公共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既然提到国家治理问题,说明我们以往的国家管理模式仍然更多的是统治的形式,而不是真正的现代国家治理。统治和治理是不一样的。
于建嵘:从农业税政府过渡到土地税政府是很大的进步,但如果没有民主和真正的代议制,很难改变现在的社会。
冯兴元:代议制很重要,民主制度很重要,感谢四位嘉宾,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