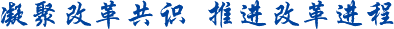晚清新文化观的演进
发稿时间:2014-05-30 00:00:00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刘悦斌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大清帝国首都、皇帝仓皇出逃、皇家园林圆明园被焚掠一空、结束战争的不平等条约等一系列让中国人感到“创剧痛深”的事件,让人们普遍意识到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李鸿章称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王韬称之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正是这种“变局”导致了中西之间的文化冲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与佛教传入时不同,西方文化(西学)是随着先进的坚船利炮和廉价的工业品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向中国的传播带有强迫性。如何认识和对待强势的西方文化,成为当时的中国人回避不开的问题;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学)何去何从,成为回避不开的又一个问题,“中西”比较引出了“古今”问题。在对中西古今的比较中,产生了新的文化观,就其发展程度说,依次有“西学中源”、“中体西用”和“中西会通”。
“西学中源”观
顾名思义,“西学中源”说认为西学源出于中国,是在中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非西人所自创。其实这种观点最早出现于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后的明末清初,但在洋务运动开始后蔚成大观,基本思路是:古老的“中学”被中国后人“失之”,而西人“袭之”并发扬光大,现在学习西学只不过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是“礼失而求诸野”,符合古圣先贤之“遗意”。洋务派在建议设立天文算学馆时说:“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土之天元,彼西土犹目为东来法。特其人情性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术如此,其余亦无不如此。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
毫无疑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西学中源”说牵强附会,是不正确的,当时即有人提出批评。但在近代化初期,它的存在几乎是必然的。一方面,它体现出在“变局”面前,受传统熏陶的开明人士提倡学习西学时的矛盾心态,为自强不得不引进西学,对涵泳其中的传统文化又割舍不下;另一方面它也是为了缓和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情绪,减轻引进西学过程中的阻力。清政府在同文馆之争中最后支持了洋务派,理由是:“习西法者,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正体现了这种作用。
“中体西用”观
“中体西用”论一般被看作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最早由洋务思想家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国富强之术。”此后,其他洋务思想家以不同的言词和概念作了同样的表述,如王韬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郑观应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上海中西书院掌教沈毓桂明确概括出这一文化观:“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提倡者的目的在以西方先进的物质手段维护中国传统的文教制度,用薛福成的话说,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在洋务派这里,“中学”固然是他们要坚守的,但是他们强调的重心却是“西学”,因为这时“中学”的统治地位还没有受到威胁,倒是“西学”需要冲破重重阻力来中国安家落户,在这里“中体西用”体现出的是积极意义。随着近代化运动向纵深进行,“西学”的范围越来越大,从最初的坚船利炮扩大到经济、教育等制度领域,到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们张扬起抑君权、兴民权、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旗帜,“中学”的核心——君主专制制度及其理论形态纲常名教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这时,张之洞抛出《劝学篇》,通篇围绕着“中体西用”展开论述,表面上调和新旧,作持平之论,实际上旨在反对兴民权,扬言“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无一益而有百害”,至此“中体西用”论的历史作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孰优孰劣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上述两种文化观同时存在,但“中体西用”论显然比“西学中源”说进步。在“西学中源”说那里,“中学”是唯一的文化,西学不过是中学的流衍,从中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天朝上国观念和自我中心意识,向西方学习显得躲躲闪闪,“犹抱琵琶半遮面”,很有些恳求别人理解、原谅的意思。在“中体西用”这里,虽然“中学”还占有绝对优越地位,但是西学已经具有独立的形态,已是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宣称西学应该学,必须学。这两种理论在同一段时间被大体上同一部分人所坚持,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
而且,这两种理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有市场,大体上,对于还没有被广泛认同和接受、阻力还很大的“西学”,提倡者仍然祭起“西学中源”的法宝,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论证说西方的宪法和议会制度在中国也是“古已有之”:“春秋改制,即立宪法,后王奉之,以至于今。……今各国所行,实得吾先圣之经义。”梁启超还特意作了一篇《古议院考》,孙中山也说过欧洲各种新文化新学说“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的话。至于“中体西用”论的声音更是一直不绝如缕,当然它的内涵一变再变。
“中西会通”观
洋务运动的目的是“自强”,但搞了三十几年,在甲午战争中却被后起的小国日本打败,让中国人感到奇耻大辱,也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反思的结果是:只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于是有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兴起,有了维新派的文化观。维新派的文化观表面上看比较复杂,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既提“西学中源”,也提“中体西用”,但他们文化观的主体是“中西会通”。康有为明确提出:“中国人才衰弱之由,皆缘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今世之学者,非偏于此即偏于彼,徒相水火,难成通才”,为了培养通才,应该“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新旧关系即中西关系)。严复提出建立新的文化应该是“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易鼎还提出了“西法与中法相参”、“民权与君权两重”等“中西会通”的具体建议。
可见,这种新文化观的要点是反对对中学和西学“非偏于此即偏于彼”的互视为“水火”的片面观点,强调应该“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将中学、西学融为一体。它突破了“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的局限,第一次将西学置于与中学平等的地位,认为中学、西学各有所长,二者应该、也可以相互融会贯通,以创造出新文化,在中西文化观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然在康有为那里,他是以今文经学和托古改制为中学的主要内容,以民权和君主立宪为西学的主要内容,将民权和君主立宪硬塞进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和孔子的改制里面去,应该说,这种“会通”是十分牵强的,实践上也是不成功的,它的意义在于开了风气之先。
进入20世纪特别是民国后,又陆续出现过“国粹主义”、“东方文化优越论”、“新旧调和论”、“全盘西化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观实际上接近“全盘西化论”)、“中国本位文化论”等形形色色的文化观,这些文化观或偏于保守,或偏于激进,“中西调和”实际上则是“中体西用”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倒是“中西会通”的文化观,虽然康有为们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还存在着很大问题,但就其理论形态来说,恐怕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