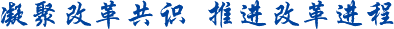亚当·斯密诞辰 300 周年:穷人改善境况的唯一希望是市场经济
发稿时间:2023-06-14 15:32:40 来源:辛庄课堂 作者: 雷纳·齐特尔曼
我们对亚当·斯密这个人知之甚少。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位著名的苏格兰人的生日。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受洗的日期:1723年6月5日(儒略历);这意味着,根据我们的公历,他在6月16日受洗。他从不知道他的父亲,一位海关官员,死于44岁,就在亚当·斯密出生前几个月。
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他的母亲,她不仅抚养他长大,而且在1784年她去世前一直和他一起生活。斯密终生未婚。我们只知道他谈过两次恋爱,但他的感情并没有得到回报,这可能是因为他被认为长得不太好看。
17岁那年,他开始在牛津大学学习六年,但对这所大学并没有留下深刻印象。他后来轻蔑地谈到他的教授,认为他们很懒惰。三十岁之前,他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并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论》。他一生只出版了两部主要著作,最著名的是 1776 年出版的《国富论》。他写的书更多,但生前手稿被烧掉了,所以我们只有这两本书和他的一些论文和讲课记录。
在那些从未读过斯密的书的人中,他有时被视为极端自私的支持者,甚至可能被视为戈登·盖科式极端资本家的精神之父,在电影《华尔街》中高呼“贪婪是好的!”。然而,这是一个扭曲的形象,源于斯密在其《国富论》一书中极力强调经济主体的私利。但这样的画像绝对是误传。
移情作为一个基本概念
《道德情操论》一书的第一章以“同情”一节开头,亚当·斯密在其中将同情定义为“对任何激情都有同感”。今天我们可能会使用“同理心”这个词。斯密说:
“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是多么自私,在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外,一无所获。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
斯密特别同情穷人。斯密从各种来源中获得收入,每年加起来高达900英镑,是大学教授工资的三到四倍。但当亚当·斯密的遗嘱被宣读时,他的外甥大卫·道格拉斯感到非常失望,收到的远低于他的预期。遗嘱证实了斯密的朋友们长期以来的猜测:斯密几乎将他的全部财产捐赠给了穷人,而且大部分是秘密捐赠的。事实上,他的慷慨甚至导致斯密自己一度陷入金钱困境。
如果你读过他的两部主要著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你将很难找到他正面谈论富人和权势的话。在他的书中,商人和地主几乎完全被描绘成负面的,他们主要是想维护自己的私利并努力创造垄断的人:
“我们的商人和大制造商抱怨高工资在提高价格方面的不良影响,从而减少了他们的商品在国内外的销售。他们只字不提高利润的坏影响。他们对自己的收益的有害影响保持沉默。他们只会抱怨其他人。”
“同行业的人很少聚在一起,即使是为了取乐和消遣,但谈话最终以反对公众的阴谋结束,或者以某种提高价格的诡计告终。”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家的正面评价比亚当·斯密著作中任何地方都多。“资产阶级不断创造出比过去所有世代的总和还要强大的生产力。”马克思和恩格斯钦佩地写道。斯密的作品中没有这种钦佩的痕迹。相反,富人是尖刻批评的目标。斯密的捍卫者认为,这并不反映对企业家或富人的任何普遍不满,而是斯密提倡自由竞争和反对垄断。这当然是一方面,但是,阅读他的两部主要著作,人们仍然会觉得,归根结底,斯密不喜欢富人就像他不喜欢政客一样。甚至亚当·斯密也未能摆脱知识分子传统上对富人怀有的怨恨。
对穷人命运的同情
然而,相反地,斯密有许多段落表现出对“穷人”状况的同情。他并没有将自己局限在最严格意义上的穷人,他也关注“不富有的人”,“即, 绝大多数人的状况,他们必须用劳动换取工资才能谋生。” 在《亚当·斯密的美国》一书中,Glory M. Liu 回顾了人们对亚当·斯密的接受和研究现状:“几乎一致认为,对斯密来说,商业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是它改善了穷人的状况。”
《国富论》中有一句名言:“没有哪个社会一定是繁荣幸福的,社会成员中的绝大部分是贫穷和悲惨的。此外,为全体人民提供食物、衣服和住宿的人,应该分享他们自己大量劳动的产品,使他们自己的食物、衣服和住宿都过得很好,这是公平的 。”
今天,这些话有时会被误解为斯密提倡政府主导的财富再分配。那不是他的意图,他当然不是在呼吁社会革命。但根据斯密的说法,贫困并不是注定的。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不信任政府。在《国富论》第8章连同上面引用的句子,他指出提高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经济增长。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提高工资的唯一途径,经济停滞导致工资下降。在另外的地方,他写道:“饥荒从来都不是由任何其他原因引起的,而是政府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来弥补饥荒带来的不便的暴力行为。”250 年后,在数百次(如果不是数千次)尝试通过价格控制来控制通货膨胀的失败尝试之后,我们完全清楚他是多么正确。
斯密写道,“劳动的自由报酬”是“财富增加的结果”,并一再强调“当社会朝着进一步获得……前进时,劳动穷人的状况,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状况,似乎是最幸福最惬意的。静中苦,衰中苦。”
另一方面,卡尔·马克思认为他已经发现了各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垮台的经济“规律”,例如“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或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在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表述如下:“随着资本大亨的数量不断减少,他们篡夺和垄断了这一转变过程的所有优势,苦难、压迫、奴役、堕落和剥削的现象越来越多;但工人阶级的反抗也随之增长,这个阶级的人数总是在增加,并且受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机制的约束、团结和组织。资本的垄断成为生产方式的束缚,而生产方式是在资本垄断的影响下产生和繁荣的。生产资料的集中化和劳动的社会化最终达到了与资本主义外衣不相容的地步。这外壳被炸裂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敲响了。……但是,由于自然法则的无情性,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它自己的否定。”
1776 年《国富论》出版时,资本主义仍处于起步阶段,绝大多数人生活在赤贫之中。贫困在当时的含义与今天截然不同。人们瘦弱且骨骼较小——纵观历史,人体已经适应了热量摄入不足。安格斯·迪顿 (Angus Deaton) 在他的《大逃亡》(The Great Escape) 一书中写道:“18世纪的小工人,实际上陷入了营养陷阱;他们不能挣很多钱,因为他们身体虚弱,他们吃不饱,因为没有工作,他们没有钱买食物。”
有些人对前资本主义条件下和谐的慢节奏生活赞不绝口,但这种慢节奏主要是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导致身体虚弱的结果。据估计,200 年前,大约 20% 的英法居民根本无法工作。“他们至多有足够的精力每天慢走几个小时,这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迫过着乞讨的生活。”1754 年,一位英国作家报道说:“法国的农民远非富裕,甚至没有必要的生存条件;他们是不到四十岁就开始走下坡路的男人。......对法国劳工来说,光是外表就证明了他们身体的恶化。” 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也类似。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劳代尔(Fernand Braudel)说:“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饥荒;长期营养不良;和可怕的流行病。” 在几十年里,死亡人数甚至超过婴儿出生人数。人们的“所有物”仅限于一些简陋的物品,如当代绘画中所见:几张凳子、一条长凳和一个充当桌子的桶。
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极端贫困中。1820 年,全球约 90% 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中。今天,这个数字不到 9%。最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十年来,自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计划经济结束以来,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达到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速度。1981年,绝对贫困率为42.7%;到 2000 年,它已经下降到 27.8%,而今天低于 9%。
事实证明史密斯是对的
斯密预测,只有市场的扩张才能带来繁荣——而这正是计划经济结束以来所发生的事情。仅在中国,私有财产和市场的引入已将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从1981年的88%减少到今天的不到1%。当我问北京大学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张维迎,斯密对中国的意义有多大时,他回答说:“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十年的快速发展是亚当·斯密市场观的胜利。” 与西方流行的解释相反,张维迎解释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主要是私有财产的引入带来的。谈到政府干预的作用时,他说,我们不应该把“尽管”(in spite of)当做“因为”(because of)。
另一个最近体现市场经济优势的例子是越南。从一个在 80 年代后期推出自由市场改革之前无法生产足够的大米来养活本国人口的国家,越南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国之一,也是主要的电子产品出口国。越南1990 年的人均 GDP 为 98 美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仅次于索马里(130 美元)和塞拉利昂(163 美元)。在经济改革开始之前,每一次歉收都会导致饥饿,越南依靠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支持和苏联和其他东欧集团国家的财政援助。直到 1993 年,79.7% 的越南人口仍生活在贫困之中。到 2006 年,该比率已降至 50.6%。今天,它只有百分之五。越南现在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充满活力的经济为勤劳的人民和企业家创造了巨大的机会。
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而不是再分配或政府法令的统治——指明了摆脱贫困的道路这一事实一再得到证实。1989 年,波兰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波兰人平均每月收入不到 50 美元——这甚至不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均收入的十分之一。即使考虑到购买力的差异,1989 年波兰人的收入也不到西德人的三分之一。波兰人比加蓬、乌克兰或苏里南的普通公民更穷。波兰的收入甚至落后于共产主义国家:其人均 GDP 仅为捷克斯洛伐克收入水平的一半。
2017年,经济学家马钦·皮亚考斯基(Marcin Piatkowski)出版了《欧洲的增长冠军》一书,他在书中盘点了波兰25年的改革:“然而,25年后,波兰成为了无与伦比的转型领导者,成为欧洲和世界成长冠军。自 1989 年开始转型以来,波兰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波兰的人均GDP增长了近两倍半,超过了所有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和欧元区。”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89年波兰人均GDP是美国的30.1%,到2016年已经上升到美国的48.4%,这种进步已经体现在人们的生活中。经购买力调整后,波兰人的收入从 1990 年的约 10.300 美元增长到 2017 年的近 27.000 美元。与欧盟 15 国相比,波兰人的收入在 1989 年不到三分之一,2015 年已上升了近三分之二。
亚当·斯密对国家的不信任
卡尔·马克思相信只有废除私有财产才能改善穷人的状况,而斯密则相信市场的力量。他不是没有国家的自由意志主义乌托邦的倡导者——他相信政府有重要的职能要履行。然而,在1755年,也就是《国富论》问世前二十年,他在一次演讲中警告说:
“人通常被政治家和规划者视为一种政治机制的材料。规划者在处理人类事务的过程中扰乱了自然;其实只需要让她独自一人,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给予她公平的竞争,她就可以制定自己的计划……所有阻碍这一自然进程、将事情推向另一条渠道或努力、在特定点上阻止社会的进步的政府,是不自然的,为了养活自己就不得不压迫和专制。”
这些确实是预言性的话。规划者常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抱有可以在纸面上规划经济秩序的错觉。他们相信,一位坐在办公桌前的作家可以塑造一个理想的经济秩序,剩下的就是说服足够多的政治家在实践中实施这种新的经济秩序。
哈耶克后来称这种方法为“建构主义”。他说:“理性的人坐下来考虑如何改造世界的想法可能是这些设计理论最具特色的成果。” 根据哈耶克的说法,斯密与大卫·休谟和亚当·弗格森等其他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分享的对历史事件的反理性主义洞察,“使他们第一次能够理解制度和道德、语言及法律是如何通过一个过程演变的累积增长,只有在这个框架内,人类理性才能成长并成功运作。”
以经济史学家的方式,斯密描述了经济发展,而不是勾勒出一个理想的制度。
计划经济学正在迎来又一次复兴。气候保护倡导者和反资本主义者要求废除资本主义,代之以计划经济。否则,他们声称,人类没有生存的机会。在德国,一本名为《资本主义的终结》(Das Ende des Kapitalismus)的书成为畅销书,其作者乌尔里克·赫尔曼 (Ulrike Hermann) 已成为所有脱口秀节目的常客。她公开提倡计划经济,尽管这在德国已经失败了一次——就像其他任何地方都试过的一样。与古典社会主义不同,在她的计划经济中,公司没有被国有化,它们被允许保留在私人手中,但正是国家明确规定了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
将没有更多的航班,也没有更多的私人汽车。国家几乎决定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将不再有任何单户住宅,也不允许任何人拥有第二套住房。新建筑将被禁止,因为它对环境有害。取而代之的是,现有土地将“公平”分配,由国家决定每个人的土地面积。肉类消费只能作为例外被允许,因为肉类生产对气候有害。一般来说,人们不应该吃太多。Herrmann 说,每天摄入2.500卡路里的热量就足够了,她建议每天摄入500克水果和蔬菜、232克全麦谷物或米饭、13克鸡蛋和7克猪肉。“乍一看,这份菜单似乎有点简陋,但如果德国人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他们会更健康,”这位资本主义批评家安抚道。既然人人平等,他们也会很高兴:“配给听起来很不愉快。但也许生活会比今天更愉快,因为正义使人们幸福。”
看不见的手
今天,斯密经常因强调自身利益的重要性而受到批评。他强调自私的重要性,正是因为人无时无刻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不过,他认为,人这样做,不能单靠别人的善意。顺便说一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使用了“看不见的手”这个词,他因此而出名,尽管这个词在斯密的整个作品中只出现了三次(顺便说一句,这类似于熊彼特和他只用过两次的短语“创造性破坏”):
“所以,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加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这种利益。……在这场合,就像在许多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尽力实现一个并非本意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经营交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劝阻他们。”
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强调,将利己行为与利他行为进行对比是错误的。他解释说,幸运的是, “我没有选择自己的行为和举止是为自己服务还是为我的同胞服务的权力。……如果是这样,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将亚当斯·斯密 (Adams Smith) 对科学思想的最大贡献描述为——指向远远超出经济学的领域——“他的自发秩序概念可以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样创造出复杂的结构。”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试图削弱“我”。正如国家社会主义的两条格言所示:“Du bist nichts, dein Volk ist alles”(“你什么都不是,你的人民就是一切”)和“Gemeinwohl” vor Eigenwohl”(“公共利益优先于自身利益。”)阿道夫·希特勒在1930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说:“在整个经济生活领域,在整个生活中,人们必须摒弃个人利益是最重要的东西,整体利益建立在个人利益之上的观念,即个人利益首先会带来整体利益的观念。恰恰相反:整体的利益决定个人的利益。…… 如果不承认这一原则,那么自私必然会滋生并撕裂社区。”
这一信念将所有极权主义思想家和独裁者团结在一起。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在她的著作《论革命》(On Revolution) 中写道:“不仅在法国大革命中,而且在其榜样所激发的所有革命中,共同利益都以共同敌人的名义出现, 从罗伯斯庇尔到后来的激进主义者的恐怖理论都预设了整体利益必须自动地,而且实际上是永久地与公民的特殊利益敌对。” 是的,荒谬的是,阿伦特声称无私是最高的美德,一个人的价值可以根据他违背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意愿行事的程度来判断。
对亚当·斯密的批评
斯密是一位先驱,他的工作为后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奠定了基础——哈耶克和米塞斯对他非常尊重。但斯密的工作也遭到了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圈内的尖锐批评。自由意志主义的美国经济学家默里·N·罗斯巴德 (Murray N. Rothbard),在他的巨著《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思想》中,毫不掩饰地诋毁斯密,认为斯密绝不是他通常被描绘成的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倡导者。事实上,罗斯巴德声称斯密错误的劳动价值论使他成为卡尔·马克思的先驱,并声称马克思主义者肯定有理由引用这位苏格兰哲学家并将他作为他们自己的开国元勋的最终灵感来源。根据罗斯巴德的说法,斯密未能理解企业家的经济功能,甚至达不到理查德·坎蒂隆等经济学家提供的见解,支持国家对利率施加上限,对奢侈消费征收重税以及政府广泛干预经济经济。在个人层面上,罗斯巴德说斯密也不值得信任,因为他以前曾为自由贸易而竞选,但在他生命的最后 12 年里,他一直担任苏格兰海关专员。
大部分批评当然是有道理的,但称亚当·斯密为左翼分子是错误的。就连强调斯密左翼倾向的美国哲学家塞缪尔·弗莱沙克也承认,斯密不一定会认同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者或捍卫现代福利国家。
反对这种批评的是斯密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极度不信任,以及他对引导市场走向正确方向的“看不见的手”几乎无限的信心。根据斯密的说法,当经济崩溃时,绝不是由企业家和商人造成的,而总是由国家造成的:“伟大的国家永远不会因私人而变得贫穷,尽管它们有时会因公众的挥霍和不当行为而贫穷。”他在他的主要著作《国富论》中写道。他乐观地补充说:“每个人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做出的统一、持续和不间断的努力,公共和国家以及私人富裕最初源自的原则,往往足以维持事物趋于改进的自然进步,尽管存在政府的奢侈浪费和最大的行政失误。就像动物生命的未知原理一样,它经常使体质恢复健康和活力,尽管不仅有疾病,而且有医生荒谬的处方。”
这个比喻说明了很多:私营经济参与者代表着健康、积极的发展,而政客们则通过荒谬的监管来阻碍经济发展。如果亚当·斯密今天看到欧洲和美国的政府越来越多地干预经济以及相信他们比市场更聪明的政客,他会非常怀疑。
斯密的缺点之一是他不了解企业家的经济功能,这一点后来被约瑟夫·熊彼特等思想家精彩阐述。他错误地认为企业家主要是管理者和商业领袖,而不是创新者。史密斯认识到“同理心”的重要性,但他在工作中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将其等同于企业家精神。今天,我们在史蒂夫·乔布斯和其他比客户自己更早地了解客户需求和感受的企业家身上看到,同理心——而不是“贪婪”——确实是创业成功的基础和资本主义的基础。
斯密未能理解企业家的角色,以及他对富人明显的不满,这确实是斯密与政治左翼人士的共同特征。然而,这根本不适用于他提倡改善工人条件。因为,在斯密看来,改善普通民众的处境不可能通过再分配和过度的国家干预来实现,而是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而经济增长反过来首先需要一件事:经济自由。随着经济自由的普及和市场的扩大,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斯密诞生300年后,他的巨著出版约250年后,我们知道这位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是对的: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是增长的基础,如果国家不过多干预经济,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改善,尤其是穷人的生活。
自由市场的支持者未能准确地将这些相关性置于他们捍卫市场经济的核心:需要市场经济的主要不是强者,因为在任何体系中他们总会以某种方式活得滋润,而是弱者和穷人,他们改善生活条件的唯一机会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