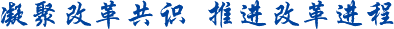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如何演变的?
发稿时间:2023-10-16 14:20:15 来源:《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作者:张晋藩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有一条纵向传承、革故鼎新的螺旋式上升的轨迹,中央地方关系也同样沿着这条轨迹不断发展。秦统一后建帝制,“海内为郡县”;汉代实行强干弱枝的中央地方制度;唐朝中央机构实行三省制,地方机构实行州县二级制;宋朝总体而言,实行二府制与地方兼施制;元朝在民族大一统的局面下,地方制度为行中书省制;明朝中央为内阁制,地方行路、州、县三级制;清朝的中央地方关系具有鲜明的民族统治的特点。中华民族是古代中国大一统体制政治实践和理论学说催化而形成的,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在这方面积累的历史经验很有借鉴意义。
大一统的政治制度适合中国传统国情,有助于民生的改善和文化的统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专制主义的皇帝制度,推行郡县制的地方制度。虽然秦朝转瞬亡国,但它留下的制度无论中央的皇帝制度还是地方的郡县制度,一直传承于后世,历时两千多年。这充分说明了这个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需要。以中央地方关系架构之初来看,秦始皇建立的皇帝制度和推行的地方郡县制度,都是周朝宗法分封制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秦始皇即位以后,天下并未平定,百姓的温饱与安居尚如空中楼阁。在这个背景下,本应运用新建的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安抚百姓,助力民生,维持社会稳定。然而,秦始皇却自以为“天下莫予毒也”,肆行独裁统治,压榨民生,耗尽民力,以致“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曾经是改革推动力的法制,反而变成了虐害民众的枷锁,形成了“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的惨象。这是一个关于控制与征服的魔咒,资源一旦过于集中,一定会利用它压迫别人。作为新生的专制主义的皇帝制度,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却成了秦始皇推行暴政的工具。他把中央集权制度看作是皇帝个人集权专制和滥施淫威的工具,无限制地膨胀皇权,加强中央的集权,最后把新型的皇帝王朝引向了灭亡的绝路。秦之亡并不是亡于制度,而是亡于破坏了制度。
汉朝建立以后,比较注意全面发挥皇帝制度的法定权力。如遇重大事项召集朝议、朝会,皇帝与大臣共同协商,决定之后迅速推向全国。汉初的做法有利于发挥皇帝制度的动员力量,可以迅速调整地方上不利于中央集权的一些弊政,改变了百姓对皇帝制度的看法。历史证明,专制主义不等于皇帝独裁,由汉朝建立的朝议、言谏、封驳制度,有利于发挥皇帝制度中的积极因素,有助于迅速推进国家各领域的发展和建设,并使皇权的行使受到制度的和法律的某种约束。因为皇权受到约束,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才延续下来。只是到了明清两朝,随着宰相制度的废除,皇帝制度的恶性发展,专制主义的国家制度也很难维持下去。破坏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将其变成个人暴虐独裁载体终而覆亡的元凶,不是别人,正是皇帝自己。
在中国历史上提及地方行政,向以汉代为榜样,称道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得当,体制合理。西汉加强中央集权的结果,使得对外有足够的力量抵御外患,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对内消除了地方割据势力,保证国内各个地区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不断加强,从而使统一的封建国家更加稳固,社会经济更加繁荣。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二年西汉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余人,疆域东西九千三百零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经过四百年的创造和发展,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封建国家,在距今两千年之前已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从此以后,国家的统一成了历史发展的主流。
中国悠久的历史证明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的制度作用,重在修制选人
所谓修制,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及时剔除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证明不适合中国政治实际的某些制度。同时需要明确,制度是死的,更重要的是执掌制度的官吏的素质,是否能发挥制度之所长,使制度与法制、政情相统一。因此,历代都重视选官的问题。因而,汉唐以来,对郡县长吏非常重视。
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是古代中国行政管理的重要问题。为了实现中央集权,中国古代很早便形成了大一统的理论和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就是强调用人权、发兵权、立法权、财政权收归中央。而当这些权力实实在在由中央政府掌握时,国家的统一也更加稳固。为了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很注意运用统一的法律法令,对地方官明定权责,进行监督,并协调各民族间的关系。在经济方面,除掌握重要的生产资料和官营工商业外,也赋予地方经济以发展空间。在文化方面,则始终坚持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一元化的文化传统。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大都是中央政府有效地行使行政管理权的时期。但是中央的权限过分集中,像秦朝那样“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破坏了中央与地方的正常关系,束缚了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使地方政权失去了活力,造成政事臃塞、冗员充斥、国力衰微,进而削弱了中央集权。而如果地方权力过大,外重内轻,中央政府不能节制,也会导致地方割据自为、王朝崩溃、国家分裂、社会动乱与人民颠沛流离。东汉末年的州牧擅权,唐末的节度使专政就是明证。因此,封建统治者煞费苦心地调整二者的关系,一方面赋予地方政权处理兵刑钱谷的一定权力,规定省、郡、县各级政权的管辖范围和从属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调专制主义的集中制,有关地方官吏的选任、军事的调动、法令的适用、死刑的执行、赋税的大笔支出、重要工程的兴造等等,均须报中央政府,以便居中驭外,内外相维,特别是清朝,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辖、司法管辖深入到边陲之地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很值得重视。但由于封建国家的本质,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在行政权力上的矛盾只能作某种调整而不可能解决。当今,在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为了更好地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认真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是很有必要的。
监察制度能够沟通中央与地方,官和使紧密结合,形成监察网络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产生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它在中国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以忽视的。
监察制度从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经过秦汉,已经奠定了规模。至唐朝,不仅完善了监察制度,而且使监察系统网络化,全面涵盖了中央和地方。如同史书所说,中国的国家体制,是“设官以经之,置使以纬之”。“设官以经之”,是指设置于地方上处于“静态”的地方官。“置使以纬之”是指巡按御史或按常例进行巡察,或奉圣命进行专项监察,是“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
监察官历来被称作是“皇帝耳目之司”,求治的皇帝非常重视选拔监察人才,有时由皇帝亲自面试。从唐朝开始,确定监察官必须科第出身,忠诚廉洁,敢于纠弹不法。由于监察官是流动的,是遍及全国各地的,地方各级政权机关都摆脱不掉监察官的监察,因此,监察官对于吏治起着震慑的作用,而且,借助监察网络,沟通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历史上,宰相受到监察御史的弹劾而去职者,比比皆是。为了掌控地方官的活动,秦始皇就专派监郡的御史。汉初,曾经撤销了设在郡上的监御史,但不久便发现,失去监御史的郡吏治很快混乱,监御史制度随即恢复,而且,中央不断派出巡御史察郡。汉武帝时,首定监察法《六条问事》,首要对象就是二千石的高官、郡守。至唐代,制定《巡察六条》,监察不再限定于郡守,而是“是官皆监”。清朝详定了监察法法典,这是中国古代具有特殊价值的一部法典,是世界上其他各国所没有的。晚清官制改革,旧官制基本都被废除,但保留都察院不废,说明监察制度在晚清仍然发挥着基本的职能,如炙手可热的庆亲王奕劻,便被监察御史弹劾贪污。
总之,在中国的政治史上,官吏的活动是重要的政治轨迹。正如孟子所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没有治国的好官吏,也不会有治世的出现。制度设计得再好,没有良吏也都会落空。
两千年来,地方政权虽不断地发生变动,但郡县制度总体是稳定的
自秦统一以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地方政权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地发生变动,或郡、县二级制,或省、郡、县三级制,或省、道、府、县四级制,但无论怎样变动,其目的都是为了适应中央集权,在变动中郡县制度总体是稳定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路径模式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省、道、府、县的四级政权中,省、道、府的任务是治官,并不直接接触百姓,而是希望通过治官达到治民的目的。只有县官是直接临民的,县是最低一级政权,县令长是亲民之官,直接掌握乡里基层组织,特别是督率乡之三老进行教化,督率啬夫重视农业生产,举办乡宴聚会以敦老幼之序。县官既担负如此重要的职责,对县官的选任、考绩就非常重要。
明太祖特别颁布法律规定州县临民之官的具体要求。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制定“府州县条例八事,颁示天下,永为遵守”。其中强调各级官吏都要加强管理,提高统治效率,以及上级对下级的监督等等。尤其重视作为基本行政单位的县的吏治,曾经刊布《到任须知》三十一条,其中规定:县官到任首先要了解刑、版籍、田粮等关系到封建国家根本的司法、财政事项;其次要了解“境内民人犯法,被诛者几户”以便掌握县内居民的政治情况以加强监视,防止发生危害国家统治的行为。对于府、州、县官中的廉洁正直者,“必遣行人赍敕往劳,增秩赐金”。以上充分反映了明朝统治者对于加强地方机关统治效能的经验的积累,这些措施旨在加强地方官的职责,发挥护一方稳定、保一方平安的作用,而不纯为防范地方豪强势力。民生福祉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在发展民生中赢得民心,是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巩固统一的基础。
从中国传统历史论,应当学习汉唐,汲取宋明教训,注重总结地方官吏治绩,注重发挥地方“以藩屏周”的重要作用。“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国政治上最大一问题。因为中国国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坏,关系最重要。”顾炎武在明亡国后,痛定思痛反思道,国家根基在基层,在基层临民之官,“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
“溯往知来”。维护国家大一统格局,中央地方关系因时调整是历史的规律。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就短时效益来看是广大普通民众,就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则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坚持党的领导,在中央地方大一统的格局中,让中华民族像石榴籽一样抱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族复兴、国祚绵长、文明传承,需要我们以史为镜,学史明智。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