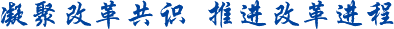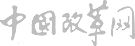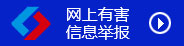经济外交:全球竞合新动向
发稿时间:2014-03-03 00:00:00
经济外交作为国际关系领域一个概念,据学界考证,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由日本岸信介政府首先提出的。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在国际政治舞台难以施为,便在经济上大做文章以拓展外交空间。这一概念迄今无权威和统一的定义,但粗略说来,国际交往中,以经济手段达到外交目的,以外交手段达到经济目的,抑或二者兼具,均可纳入经济外交范畴。
自古有邦国即有外交,有外交其实即含有经济外交的成分,中国远追春秋管仲,西方直溯希腊罗马。但现代意义的经济外交,公认始自民族国家崛起之后。二战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被认为是经典案例。上世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迅猛推进,各国普遍转向经济层面的竞争,日益注重以外交促经济促发展。2013年中欧光伏争端的和解,领导人亲自推动的经济外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3年是国际金融危机第5年,各个领域的国际竞争都在加剧,经济外交高度活跃。从全球层面来看,经济外交的竞合博弈正在“升级换代”,手段与目的都在跨界、融合,而最富经济活力和政治复杂性的亚太地区,已成经济外交的最前沿。这一趋势在未来数年将更加清晰。
2013年多国经济外交强势出击
2013年的全球经济外交,呈现两个重要特征。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多国强化了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将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另一方面,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合博弈中,经济外交与安全、政治、军事等议题的互动更密切,全球经济外交更加借重金砖机制、G20峰会等多边平台,更多元、更宽广。
2013年1月底,约翰 克里被提名为美国新任国务卿。他在国会参院听证会上阐述其未来4年外交构想时,断然宣称“经济政策即外交政策”,指出美国外交政策不应仅仅定义为无人机和军事部署,全世界都在竞争资源和市场,美国如果不愿投入这些领域,只会自我削弱。美智库亚洲学会当即把克里的表态称为“外交新思路”。
2013年是俄罗斯“入世”元年。据俄外交部外交学院教授马克 奈马克撰文介绍,克里姆林宫在2013年外交构想中,首次把俄外交政策的经济方面概括和具体表示为“经济外交”,并提出新的目标——巩固俄在欧洲与亚太经贸联系中关键的过境国地位,新的重大地缘政治措施——组建欧亚经济联盟。岁末,俄罗斯围绕乌克兰与欧盟“拔河”成功,经济外交告捷。
梳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一年来的出访路线图,不难看出,经济外交和围堵中国是其主要着力点。2013年4月访问俄罗斯和中东时,安倍就盯住日本的能源稳定供给与核电和医疗技术出口,期望打响“经济外交的第一发炮弹”。为围堵中国,安倍游走东南亚,在价值观外交的幌子下,“对东盟大把大把撒钱”。仅12月日本—东盟特别峰会上,安倍便宣布今后5年内将为东盟提供总值2万亿日元经援,另与东盟十国均签署了投资协议。日本《朝日新闻》说,安倍“摆出一副财大气粗的架势”,“但能否给日本带来实惠,却是一个未知数”。尽管如此,安倍政府显然已摆出在东南亚地区全力进行经济外交的姿态,并把经济外交的主要竞争对手明确定位为中国。
2013年11月底,加拿大政府向外交人员发布新训令,主题词即为经济外交,要求所有驻外人员以推动国家商业利益为第一优先要务,重中之重是改善加拿大在新兴市场贸易及投资的不足,5年内将在中国、印度及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小企业数目增加一倍。加国际贸易部长法斯特说,如果这一五年计划成功,加拿大能创造4万个与外销有关的新工作。
2013年英法经济外交的“王牌亮点”也在亚太,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法国总统奥朗德2012年上台不久就宣布,经济外交是法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他2013年2月访问印度时,力促印度向法购买126架“阵风”战斗机的谈判,并谈成了法国为印度军队研发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合作协议。两个月后,奥朗德又“带了整整一飞机的商人”访华,促成民用核能和航空等领域一系列合作。
卡梅伦也在2013年2月展开任内对印度的第二次访问,努力扩大对印投资渠道,试图构建英印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特殊关系”。12月初,他又率上任以来最大出访团组来到中国,携投资、金融、司法等领域合作文件与经贸大单满载而归。
一年来,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强力推动下,中国经济外交成绩斐然,仅与各国达成的合作协议就多达近800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重大合作倡议,成功引领了区域合作方向。
2014年全球经济外交重要动向
与过去10年和20世纪相比,2013年的全球经济外交显现三个重要动向,势将在新的一年里延续和深化。
首先,周边和多双边自贸谈判成为主要国家推进经济外交的重点抓手。
这方面,最突出的是美国。美国经济外交的主要抓手就是跨越东西两大洋的自贸谈判,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2013年俄罗斯一直致力于落实年初生效的《独联体自贸区协议》。继乌兹别克斯坦5月正式加入后,吉尔吉斯斯坦12月也正式批准这一协议。平安夜当天,普京明确要求在2014年5月1日前完成欧亚经济联盟条约草案,以便联盟在2015年元旦前全面展开工作。这一联盟实即俄罗斯主导的俄白哈关税同盟升级版,从地缘政治上看,其前锋直抵仍在试图东扩的欧盟。俄罗斯不惜血本地围绕乌克兰与欧盟“拔河”,战略着眼点实在于此。
多双边自贸在中国经济外交中地位也大幅提升。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接连访问东南亚,周边外交全面提速,打造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大幕隆重开启。李克强年内两度访欧,直接推动了中国―瑞士自贸协定的签署。一年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中韩、中澳自贸区谈判都在向前推进,中美还启动了双边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
2013年岁末传出的一个利好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消息是,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12年来首次达成初步协议。不过,对其意义应有清醒的估计,这一协议避免了多哈谈判立即死,但却不足以确保谈判活下来。就目前成果而言,难以扭转各国聚焦多双边自贸谈判的现状和趋向。
其次,在全球经济外交中,围绕国际贸易主导权和规则制定权的博弈日趋激烈。
时至今日,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大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仍远低于他们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但金融危机以来,面对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发达国家却表现得更加渴望“守成”,一心要继续掌控国际经济治理,确保国际贸易规则符合西方利益。这一战略考量,在TPP和TTIP谈判中展露无遗。两大谈判是全球现有标准最高的自贸区谈判,业界普遍认为可能引领未来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走向。新加坡《海峡时报》指出:“当前有关TPP的谈判,体现了美国在投资、竞争政策、劳动标准、政府采购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利益。”
发达经济体作为既得利益者,希望“守成”,继续主导国际贸易格局;新兴和发展经济体则希望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更多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以利于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新兴和发展经济体这一要求的正当性质是不容否定的。如果不去除国际经济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因素,全球经济的活力与潜力势必难以释放。中国政府已表示,将以开放心态面对TPP等各种区域及跨区域自贸倡议,促使各方兼容并包,携手共进;但如何兼容,与谁携手,恐怕还需政策创新。
再次,亚太地区的新兴市场,特别是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外交最活跃的场所。而中国全面深化国内改革的进程,势必将带动中国经济更大程度的开放,进一步增加中国经济外交的辐射能力。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年来,不论英法德希等欧洲国家,还是韩澳加新等环太诸国,都把中国作为经济外交的重点目标。习近平主席2013年夏访问拉美之际,墨西哥副外长德伊卡萨的表态传递出国际社会的普遍心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不希望更大程度地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政府已把经济外交列为2014年外交的一大重点方向。在2014年中国经济外交的总体构想中,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创新设计尤为引人注目。这“一带一路”建设,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早期收获”,而从长远来看,不仅有助于中国构筑坚实的周边经济圈,也将成为联系世界各主要大洲、创造共同繁荣与利益的坚实纽带。
2013年,中国经济外交的总体布局逐渐明晰,周边成为重中之重,这也意味着,中日在东南亚之争将更加激烈。面对日本的“大把撒钱”,中国应保持冷静心态,避免踏入“银弹外交”、和日本比赛撒钱的陷阱,在经略周边时,更加重视多管齐下地运用综合实力。较之日本,中国在陆地接壤的东南亚占有天然的地利,更有条件在外交领域运用综合实力。况且,日本在东南亚“撒钱”,包括建设高铁,有助东南亚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数年前便指出,中国展开经济外交意义深远,因为经济力量是中国冲破其他大国围堵的最强大力量,经济手段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交往中能造成双赢局面的最重要手段。从经济外交开台来实现和平崛起的目标,亦是其他大国所没有走过的道路。
我们现在的挑战是,如何提升经济外交的质量,改善经济外交的策略,通过提升我们的巧实力、软实力、刚柔相济的综合实力,更好地配置和运用外交资源。美国智库亚洲协会学者马特 斯顿夫曾经说:“外交政策的创新是重大机遇和迫切挑战难得的结合。”就此而言,中国经济外交的政策创新,时机正在成熟。